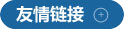当然,下面是对你提供文章的改写版本,保持原意不变,同时增加了一些细节描述,使内容更丰富,且总字数变化不大:
---
无规矩不成方圆,男女婚嫁的习俗自远古神话时代便已存在,这些传统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,从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,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婚姻仪式与契约也逐步完善,现代有结婚证作为法律凭证,古代则有结婚书作为婚姻的书面约定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宁夏黑水城遗址出土了一份元朝时期的“结婚证”,这份文书文字密集,内容详尽,达1600字之多。
仔细阅读后,人们不禁感叹:“宁死不做蒙古女子”的无奈与悲凉。
八十年代,在宁夏的西夏古城黑水城,掩埋于千年沙土之下的历史遗迹终于重新露出了它的面貌。
在这次考古发掘之前,西夏王朝一直未被广泛关注,其文化内涵也只停留在表面认识。
展开剩余91%黑水城作为西夏的重要边防要塞,曾多次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,坚守不破,显示出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。
然而,随着西夏王朝的终结,黑水城也被蒙古军队占领,城内留下了大量蒙古文化的痕迹。
到八十年代时,黑水城已成废墟残垣。
一位俄罗斯考古学者来到这里后,散布黑水城下藏有巨大财宝的传闻,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盗墓贼。
这些盗贼掠走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,并将这些文化遗产据为己有。
面对这种严峻形势,中国政府迅速组织考古队展开抢救工作,以尽量减少文物的流失。
考古队在发掘中收获了大量珍贵文物,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大批文书资料。
其中一份婚书让人们深入了解了元代乃至蒙古族的婚嫁习俗,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
早在唐宋以前,中国就已出现婚书,这标志着契约文化的萌芽。
人们为了保障自身权益,通过书写明确的约定,将婚姻事项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,这也体现了古人法律意识的初步形成。
元朝政府规定,只有持有婚书契约的婚姻才被视为合法。
由于过去频繁出现口头争执、难以取证的纠纷,婚书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凭据。
婚书不仅是订婚的依据,更是确认婚姻关系的正式契约,也是婚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俗话说:“人伦之道,婚姻为大。”
相关法律明确指出,婚书须提前约定聘礼财物,指明女婿的养老责任,规定婚姻期限,列出主婚和媒人的职责,规范书写内容以避免纠纷。
法律还特别规定,婚书中不得使用“彝北语虚文”,所有聘礼必须详细列明,男女双方及媒人均需签字画押。
女方回执婚书的要求与此相同,双方婚书背后均须注明“合同”二字,并互相保管。
若婚书内容模糊不清,或无签章及合同字样,则该婚书不被承认,等同于无效文书。
因此,古代家庭对婚书的书写和保存极为重视,历经千年,才得以保存下来数千份完整文书,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元代蒙古族在汉文化影响下,也采用婚书作为婚姻契约的习俗。
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书中,这份保存较完好的蒙古族婚书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,名为《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大吉合同婚书》。
通过阅读这份婚书,能大致了解其中的婚嫁故事。
故事主人公是太子军中一户贫苦蒙古军户的脱欢,他计划将已故弟媳再嫁他人。
古代蒙古下层军户生活极其艰苦,不仅军役繁重且无固定收入,出征时各种物资需自备。
脱欢正是如此贫困的军户,因弟弟脱火赤病故,他想将弟媳巴都麻嫁给别人,减轻负担。
巴都麻作为寡妇,生活困苦,依靠自己谋生极为艰难。
媒人帖哥牵线撮合,拟与哈立巴台成婚。
婚书中记载:“今凭媒证人帖哥作媒说合,与亦集乃路屯田张千户所管纳粮军户,吴子忠家内存日、从良户下当差、吴哈厘抛下长男、一名唤哈立巴台说合,作为证(正)妻。”
哈立巴台须赠送脱欢白米一石、小麦一石、大麦一石,并设宴款待宾客。
脱欢收下聘礼后,择吉日将巴都麻嫁予哈立巴台。
婚书还规定,若哈立巴台不善待巴都麻,罚款小麦一石;若巴都麻不服从夫家,罚白米一石。
最终,男女双方及媒人均签字画押,背后标注“合同”,婚书正式成立。
尽管婚书未见对女性的直接贬低字眼,但其内容折射出当时底层女性地位的低微。
为何如此判断?
这份婚书不同于一般的婚书。
它不是男女双方亲自签署,而是由巴都麻亡夫的哥哥脱欢代签,所承诺的财礼也由脱欢收取。
元代法律规定婚书须由新郎新娘本人签署,缺少这一点,这份婚书显得有些异常。
在婚书中,脱欢是正主婚人,巴都麻只是副主婚人,这种身份安排引人怀疑,似乎脱欢意图通过嫁人获得经济利益。
此外,这份婚书的格式也与古籍《事林广志》记载的三种婚书形式不同。
一般婚书财礼与婚约内容分开记载,且分为“纳聘书式”和“回聘书式”,而此书将两者合写,给人一种买卖契约的感觉,更像是单方面的协议。
同时,对巴都麻身份的详细描述,强调其丈夫已亡,未来改嫁无隐瞒,显现脱欢为促成婚事所做的努力。
这些细节透露出脱欢急于将巴都麻嫁出的现实考量。
学者们因此怀疑,这份婚书更接近一纸婚姻契约,甚至可视作巴都麻的“卖身契”。
因为只要条款明确,婚姻即成立,不易废止,极有可能导致强娶强嫁现象的发生。
这也反映出元代婚姻观的开放态度,改嫁、入赘、换嫁甚至冥婚都被允许,只要有婚书为凭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份同样出土于黑水城的蒙古族婚书。
文中记载,不颜帖木为自己的男仆请媒人伯刺说媒,娶孙百户家的女奴婢为正妻。
“立文字人亦集乃在城住人不颜帖木,男仆求长村住人伯剌为媒,住人孙百户扼下,妻牙糜失为正妻。”
婚书后半段同样规定了聘礼、义务及违约罚则。
“到财礼段子必甲一领,枣儿红荅环儿一对,斜雯靴子一对,酒食筵席,良成吉日成亲。如成亲已后,但有以得省口为敬,并不干不颜帖木并主婚人、贾要旁已写以先悔者罚伍拾两。”
这说明巴都麻婚书未分开写聘礼与婚约,也可能只是不同形式的婚约文本,不一定是买卖性质。
而这份为仆人说媒的婚书中,男方给予的聘礼直接交给女方本人,与巴都麻的聘礼有显著区别。
巴都麻的聘礼均为粮食,且由脱欢代收;而这份聘礼则是首饰与日用品,更贴合女方实际需求。
在古代,聘礼通常是给女方家长的,但脱欢并非巴都麻的亲属,也未养育她。
正如男仆娶女奴,女方非主人家儿女,因此聘礼交给女本人更为合适。
这两场婚姻的聘礼虽各异,但均体现了不同身份女性的婚嫁状况。
此外,这份婚书的签字画押亦与巴都麻婚书不同,男女双方均亲自签名,未分主副。
至于巴都麻是否被卖,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测。
然而蒙古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却可以较为明确地看出。
和许多封建王朝类似,女性须服从家中男性安排。
虽然她们名义上享有“改嫁”自由,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家庭结构发展的妥协安排。
参考文献:
《黑水城出土合同婚书整理研究》杜建录,邓文韬
《古丝绸之路上黑水城出土元代婚契研究》丁君涛
《“失林婚书案文卷”初探》侯爱梅
---
如果你需要,我也能帮你调整成更口语化或者正式的风格,或者帮做摘要。你觉得怎么样?
发布于:天津市